

【品傳媒娛樂時尚中心總編 & NeoFashionGo & 華人世界時報 應瑋漢 】誰是華文的主角?這個問題,早在沉默裡呼喊多年。我們習慣用普通話書寫現代,用英文接軌世界,卻忘了腳下這片土地,還有一種語言,被我們自己輕聲講、小聲唱,然後漸漸遺忘。台語,這個文明的遺珠,不是方言,也不該是遺言。普通話是國家機器打造的語言,是政權秩序的產物;而台語,則是祖母廚房裡飄出來的聲音,是千年文化被壓縮之後,仍不甘沉寂的餘韻。當我們要求 Google 翻譯新增「台語(閩南語)」選項,這不是對科技的乞求,而是對語言平權的叩問。第三種華文,不是分裂,而是復原,讓聲音回到文言文未分化之前的時間點。讓語音,成為通往古文的聲波橋梁。當 Google 能講出台語,世界才真正開始聽見它。這不是復古,而是未竟文明的接力。語言,是未來文明的密碼,不是遺忘的回音。
.
江蕙的專輯《酒後的心聲》當年銷量破百萬,震撼整個華語唱片市場。那不是一首歌的勝利,而是一種語音的集體記憶穿越被壓抑的年代,再次站上舞台的奇蹟。即使唱的是庶民、苦戀與離愁,卻賣出連台北小巨蛋都無法想像的規模。那是一場語言的逆襲,也是一場文化的覺醒。江蕙之所以能跨越語言界線感動國語聽眾,不只是旋律,而是台語裡深藏的民族情緒與古漢語語感,被她的歌聲完整釋放出來。這不是方言的魅力,而是「華語古文明的靈魂共鳴」在現代社會的一次震盪。這種演唱的力量,完全能打動跨世代、跨語族的聽眾與讀者。當她唱出《家後》、《落雨聲》、《傷心酒店》,台語裡特有的入聲、上揚、連音,就像一道語言時光隧道,牽引出我們體內早已被壓抑的「漢語靈魂」。那是一種被國語壓抑百年的古漢語音系,在江蕙的歌聲裡重獲呼吸。她不是唱出台語,她是讓我們重新聽見曾經屬於整個漢語族的語感,一種來自唐宋、繞過北京官話,依然活在市場、巷口、阿嬤耳邊的聲音。這聲音,不止屬於台灣,更屬於整個被普通話定義排除之外的語言記憶共同體。
.
台語的悲傷不喊痛,講「傷心」而不是「難過」;它說「袂凍」不是「不能」,「心肝寶貝」不是「寶貝」;那是從內臟說話的語言,是從母音裡長出來的文化。所以江蕙不是明星,她是語言的中介者,是語音靈魂的召喚師。這也是為什麼,即使聽不懂台語的人,在聽《酒後的心聲》時依然會落淚。因為那不是一句句歌詞,那是幾千年情緒的聲波,在這塊島嶼上再度共鳴。
.
江蕙讓我們理解:語言的本質,不在於誰懂,而在於誰「感覺得到」。

從語言社會學(language as cultural capital)、語言政治(language ideology)、文化認同理論(cultural identity theory)及後殖民語言觀(postcolonial language theory)的底層思考來看。在現代中文裡,我們總以為「閱讀」是眼睛的事,「語言」則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官方發音。但真正的華文經典,其實從未如此冰冷與單調。當你用台語唸出「千山鳥飛絕,萬徑人蹤滅」,那句詩突然不再只是李白的文字,而是你阿公在黃昏田埂上對你說的話。那些入聲字的收尾,如「kok」「sut」「bat」,不再是語音學裡的數據,而是一種來自歷史深處的節奏感,一種失而復得的文明氣息。我們不只是用台語說話,而是用一種被壓抑百年的漢語音系,重新召喚語言的靈魂。台語不是古老,而是未完成的時間。它穿過現代標準語音的牆,讓我們聽見另一種語言秩序,一種未被清朝官話、國語運動與科技平台剪裁過的真實。你會發現,華文經典本來就不是用普通話唸出來的。真正的語感,躲在母語的聲帶裡,藏在我們尚未習慣用科技打字的聲調之間。這不是復古,而是復權。不是鄉音,而是歷史音。讓我們用台語,重新打開華文經典的密碼庫。讓聲音先於文字,讓身體記得語言是怎麼流動的,怎麼哭,怎麼唸,怎麼愛。那不是一種方言,那是我們未竟的語言革命。
.
在這個世界上,有一種語言,沒有聯合國官方資格,也不列於全球十大通用語;卻曾在明清時期的渡船上,唸出《論語》的韻腳;在 20 世紀的街角裡,吟出《孤戀花》的絕望。這種語言,不叫普通話,也不是你我手機裡的輸入法預設。它叫台語。不是方言,是記憶。Google 翻譯,這個當代巴別塔的巨獸,能將蘇格蘭蓋爾語譯成土耳其語、將挪威語翻成馬來文;卻至今不願承認台語, 這個使用人口超過7000萬、文學、戲劇、歌曲俱全的語言,有存在的權利。那是因為它太溫柔,不吵不鬧,不上街抗議。它習慣悄悄地躲在長輩的餐桌旁,在夜市的錄音帶裡,在謝金燕的《練舞功》之間,等一個懂它的世界。這種語言作為文明載體的文化人類學視角,及將語音與文明連結,符合語言人類學強調語言是文化記憶與歷史傳承的重要工具,這是理論厚度的關鍵支點。
.
在21世紀的數位語言版圖中,「語言」不只是溝通工具,更是文化的載體、身分的記憶與科技參與的入場券。當世界進入 AI 與大數據驅動的時代,那些被排除在主流語言系統之外的「在地語言」與「母語文化」正面臨全面的數位沉默與遺忘。台語(臺灣閩南語),作為全球使用人口超過7000萬的活躍語言,卻至今未被 Google 翻譯、Apple 系統、Meta 語音模型等主流科技平台納入語言選項。這不僅是科技的空白,更是文化權利的剝奪。它是活的語言,不是死的方言 。台語在台灣、東南亞、美國及世界多地擁有完整的語言生態:日常會話、廣播媒體、流行音樂、舞台藝術與政治演說,皆活躍使用。它是古漢語的延續,連結漢字文化圈的聲音歷史 。台語保留中古漢語聲韻系統,包括入聲與文白異讀,唸古文更有韻味,是古代詩文「被說出來」的最佳管道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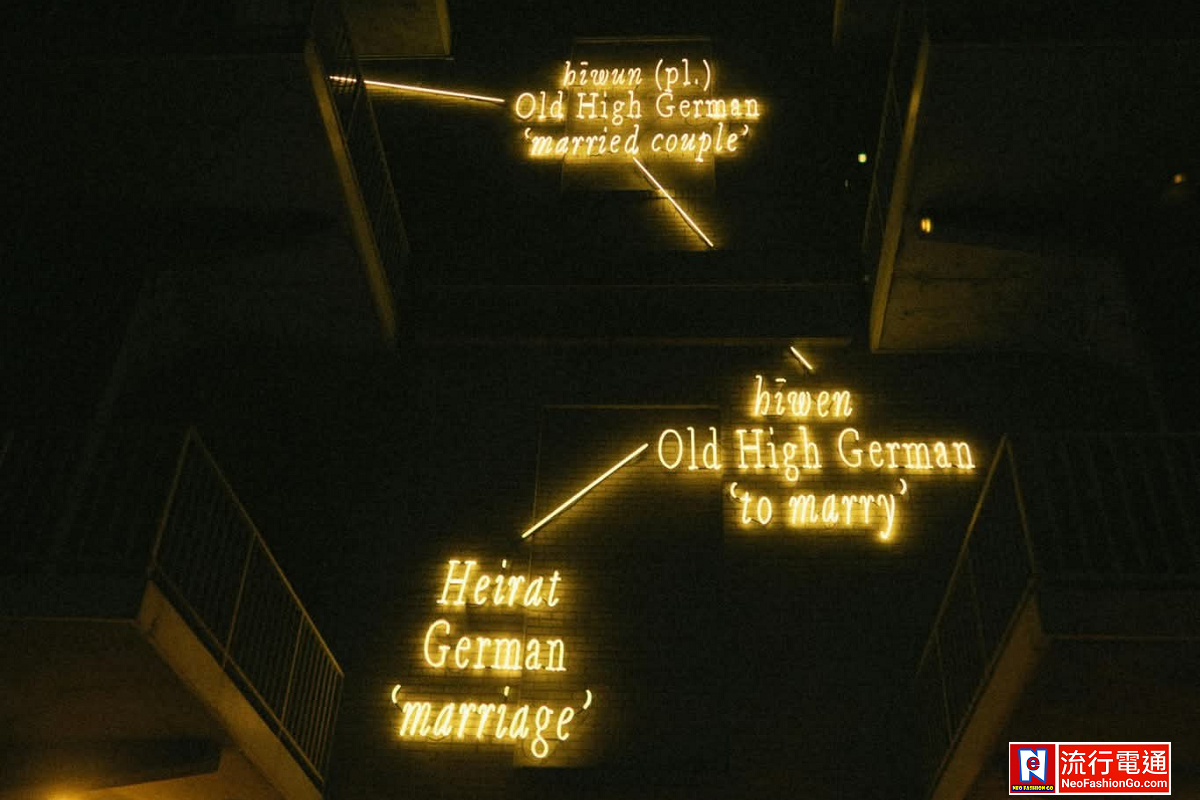
Google 翻譯新增「台語(閩南語)」為翻譯語言選項 。提供台語與繁體中文、英語、日語等語言之互譯功能,可用羅馬拼音(臺羅)與漢字混寫,兼容學術與生活應用 。強化 AI 對台語語音與語料的支持,將台語納入 Google TTS(文字轉語音)與 ASR(語音辨識)訓練目標 ,開放台語使用者語料參與語言貢獻(如 Common Voice) 。與在地語言社群合作建構開放台語語料庫與翻譯資料集。與台灣教育部、語言學者、劇場藝術家、Podcaster等合作,支援多元文體,如新聞、口語、詩歌、戲劇與民謠。長久以來,主流科技視中文為一種單一的語言體系,只區分書寫方式(繁體與簡體),卻忽略中文本質上是「同文異語」的文化複合體。台語作為閩南語系的核心語言,不僅是臺灣最活躍的日常語言之一,更是中古漢語聲韻系統的活化石。當 Google 將「中文」切分為「繁體」與「簡體」,它其實不只是為了字體差異,而是在全球數位平台上,劃出了文化邊界。而今,我們主張,中文應新增第三種分類:台語。這不是語言工程的美學提案,而是語言正義的修正行動。當平台只有兩種中文,卻少了台語這個存在已千年的語音文化,那麼所有以台語說話的家庭、創作者、學者與長輩,其聲音都將被科技世界遺忘。
.
當我們用台語唸古文、詮釋經典,意義遠超翻譯。那是一種文化的逆襲,一種「非北京語系」重新詮釋儒家、唐詩、宋詞的文明實驗。這樣的語音重構,讓「華文」不再侷限於普通話的語音支配,而是開啟去中央集權、文化多聲部的語言未來。若說普通話是語言的中央政府,那麼台語,正是被壓抑許久的地方議會,是民間筆記,是家族口述,是流浪於世界的另一本華文史。它保留入聲、文白異讀,與唐宋之間的音調脈絡。當你用台語唸《春曉》,那句「春眠不覺曉」,突然有了沉沉夜雨與土地的聲音,而不只是課本裡的朗誦。換句話說,台語不是「翻譯」中文,而是「重新解剖」中文。它讓我們看到,所謂中文,不是一種單一的語音對應文字,而是跨越時間、地域與階級的語言系譜。
.
當你打開 Google 翻譯,點開語言欄,會看到兩個熟悉的選項–「中文(繁體)」、「中文(簡體)」。這是科技平台對華文世界的語言分類邏輯:兩岸、兩制、兩種字體。但我們應該問:如果中文真的只有兩種,那「台語」是什麼?是一種被遺忘的聲音。Google 翻譯的語言清單不是中立的,而是文明的排序系統。當台語被排除在主選單之外,並非技術限制,而是文化邊緣化的結果。台語,應該被列入Google翻譯的中文分類,與繁體、簡體並列:
中文(繁體)
中文(台語)
中文(簡體)
語言不是死的規則,而是活的選擇。當一種語言能在科技平台上被選擇,它就多了一分未來的可能性;而當一種語言永遠不存在選單之中,它就被默認為「不值得被聽見」。讓我們從台語開始,打開一個顛覆華文、重寫文明的可能。Google 翻譯,不該只是全球化的工具,而應是文化多樣性的見證者。讓第三種中文,台語,成為新的文明頁章。讓我們由發起 Change.org 國際連署,將文章濃縮成精簡三語摘要(中文、英文、台語羅馬拼音)開始。Google 翻譯納入台語,它不只是工具功能的補強,而是台語第一次被「全球科技平台」所承認,成為具有國際符碼價值的語言,象徵資本的重新分配。這讓會說台語的人,開始重新理解自身語言的「可出口性」與文化價值,這是一種語言文化資本的重估。
.
殖民者與統治者從來都知道:要控制一個民族,先奪走他們的語言。
.
台灣的歷史告訴我們,語言從來不只是溝通工具,它是權力的分配器。每一次政權更替,從來不是從改寫憲法開始,而是從「你該怎麼說話」開始。日本殖民時期(1895–1945)當日本將台灣納入殖民地,首先推動的不是軍隊駐防,而是教育制度的重建——以日語取代台語、客語與原住民族語作為學校與行政語言。這不是單純的語言政策,而是一種文化消音工程。殖民政府明白:只要下一代說的話不是母親教的,就能斷開祖先與未來的連結。 國民政府來台後(1949–1990s)國語運動再次把語言變成政治的刀。學校禁止講台語,違者罰錢、戴「狗牌」,電視電台統一國語播音,報紙以普通話為書寫主體。台語成為一種「非正式語言」,被迫退縮到市場、家中與夢裡。語言的去脈絡,不只壓縮多元文化,更讓一整個世代相信:母語是不文明的,是落後的,是不該公開說的。
.
語言壓迫,是一種「記憶清洗」的戰略技術。透過語言政策改造,政權不需強迫人民改變信仰,只要改變他們說的話,就能改寫他們對歷史、家族、土地的理解。語言是一座通往文化記憶的橋,當橋斷了,民族便開始遺忘自己。如今,我們爭取的不只是保留一種語言,更是奪回一種被剝奪的敘事權:讓孩子重新認識什麼是屬於自己的語音,讓世界知道華文不等於中國普通話,讓母語不再是歷史的錯字,而是未來的起點。這是一場歷史責任,也是一場政治清醒。也隱喻語言在權力體系中被塑造與壓制的現實,符合語言權力批判理論(language power critique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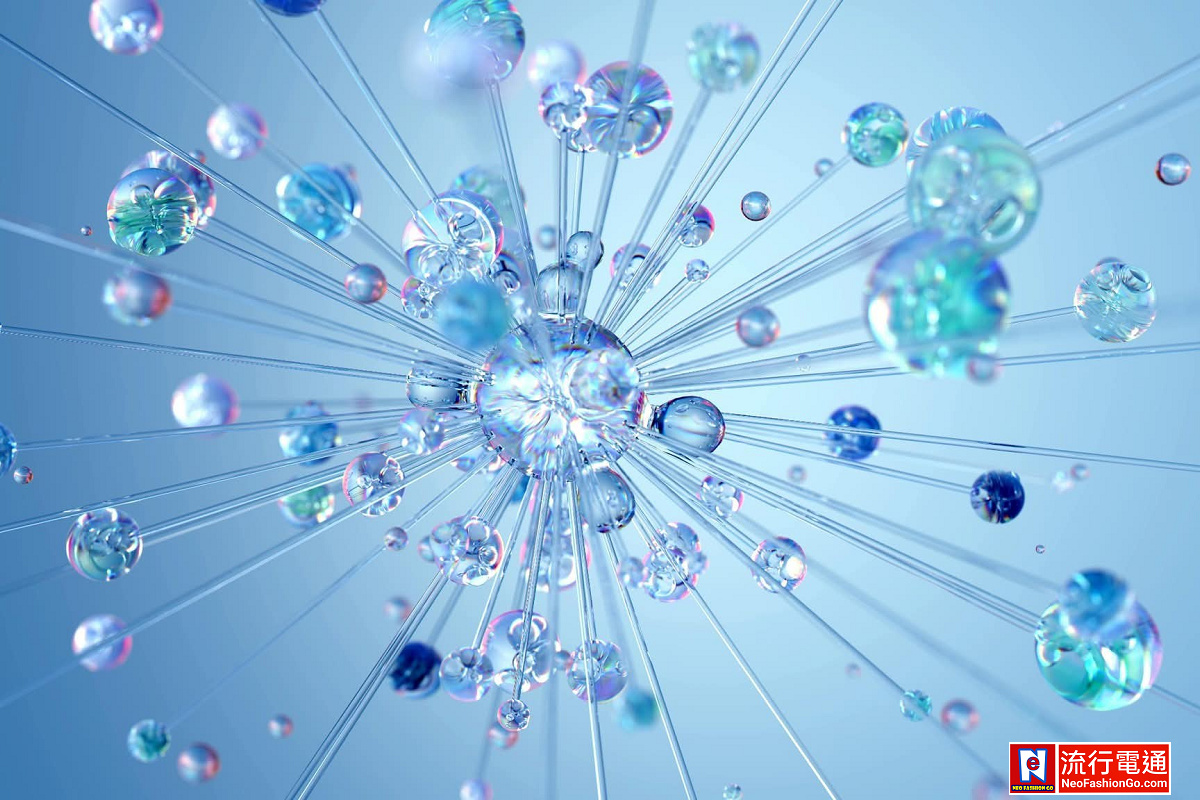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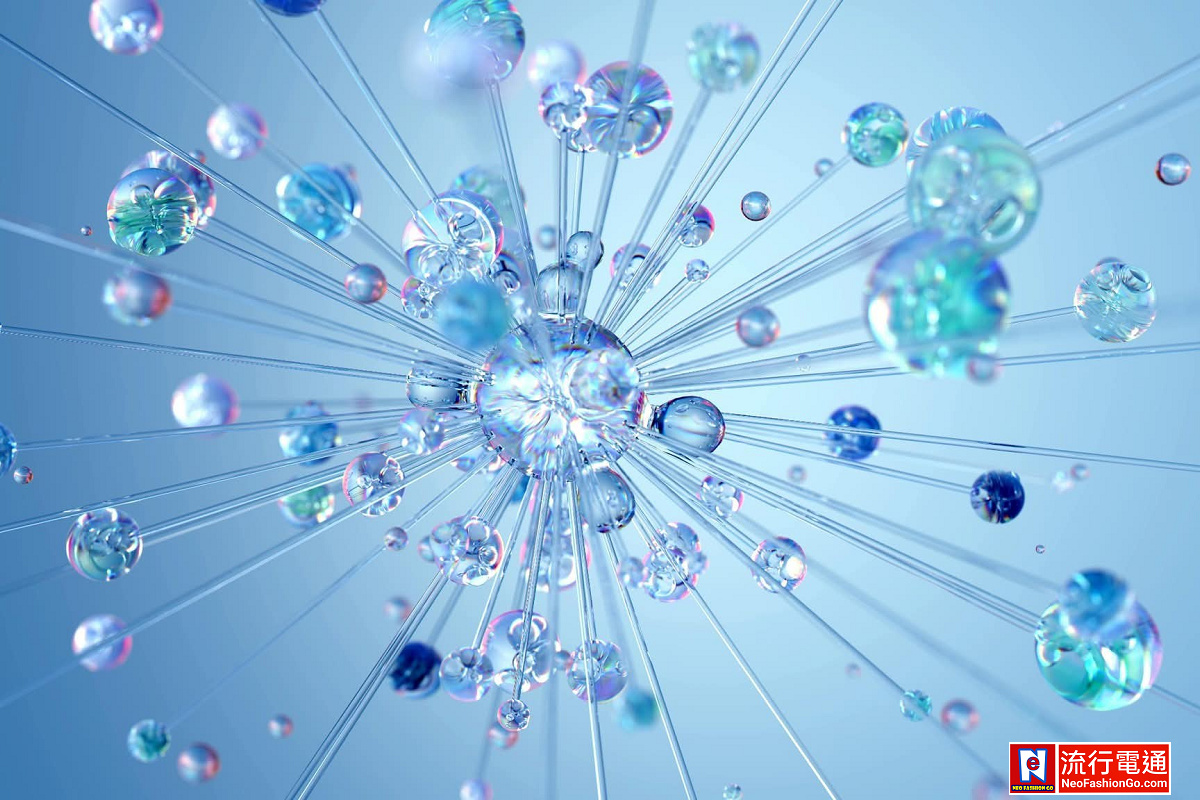
這一次,華語文化的主導權,正在重新回到台灣的島上。
.
幾百年來,華人世界的語音版圖不斷變動。北京話成為官方語言,是清朝滿人進北京後的結果,真正被推廣到全中國,也不過短短百年。國語(普通話)作為語音標準,在中國自1955年以來強制推行,在台灣則是1949年後才全面實施。這不過是兩三代人的事。相較之下,台語(河洛語、閩南語)承載的語音系統,源自唐宋,活過元明清,一路延續至今,歷經海洋遷徙,竟在台灣保存最為完整。在中國多數地區,台語的語音根已被「官話化」逐步侵蝕,但在台灣,台語卻像一種語音的種子,躲在庶民生活裡、田野市井間,持續開花、傳承。它是全世界最長時間未中斷、仍在自然使用中的華語語音系統。這不是偶然,而是歷史的修復。語言的主導權,不再被一黨、一朝、一城所定義,而是落回到了真正使用它、活出它、創作它的人身上。那,就是台灣人。台語,不只是語言,而是對「什麼是華文」這個問題,提出了另一種答案。當北京話、普通話被寫進課綱、外交簡報與翻譯系統,台語卻從來不靠權力維繫,只靠生活、靠家族、靠歌聲、靠菜市場的吆喝與老人家的訓話。
.
這是它的脆弱,也是它的力量。
如今,
當科技平台準備再定義「什麼是中文」,我們正站在一個歷史的轉折點
.
所以,這一次,我們要主動出聲。把台語送進 Google 翻譯。讓台語拼音成為全球可讀,讓孩子知道,原來我們說的話,比課本還久遠 ,這不只是語言的復權,而是一次文化話語權的逆轉工程。
.
也許有一天,當你在 Google 翻譯輸入:
「我愛你,阿母。」
它不會翻譯成英文、韓文、法文,
而是以一種你熟悉的語氣回答你:
「Góa ài lí,A-bú。」
.
在那一刻,你會知道:語言沒死,只是等我們說出來。
江蕙的歌聲,帶回了我們語音的靈魂,試圖讓台語的靈魂永遠不再沉默。
.
( EDN – 東方數位新聞- EastDigitalNews – www.eastdigitalnews.com )


